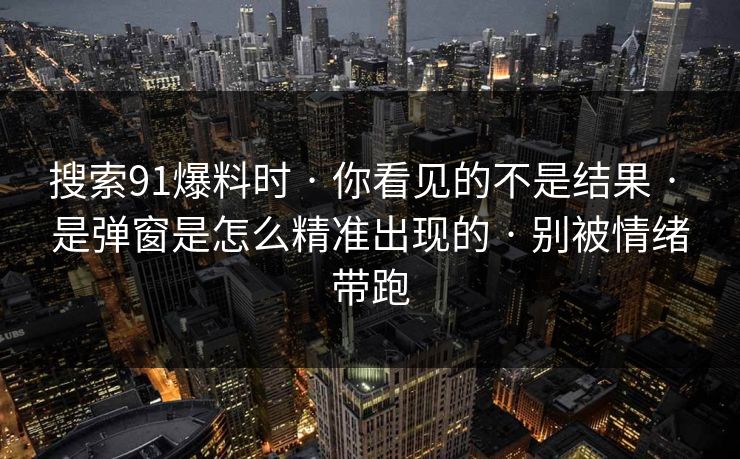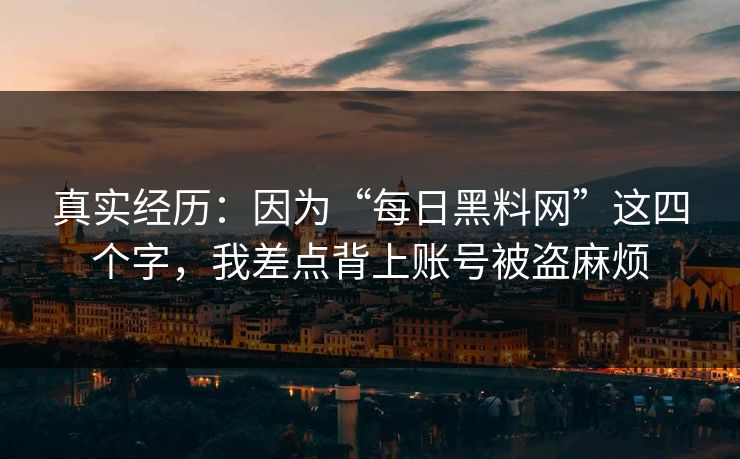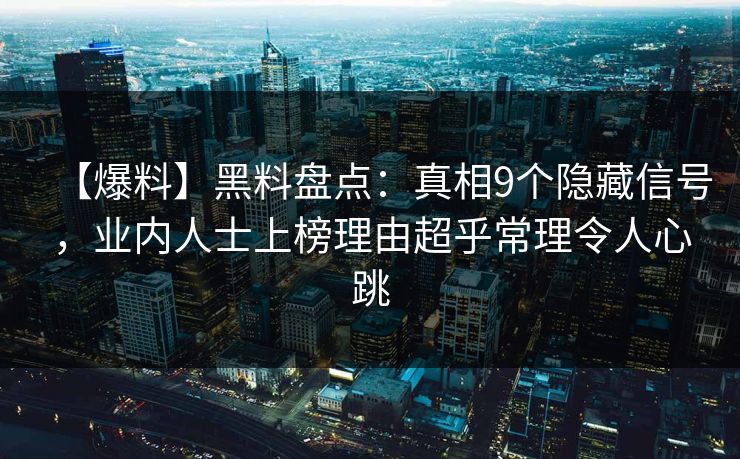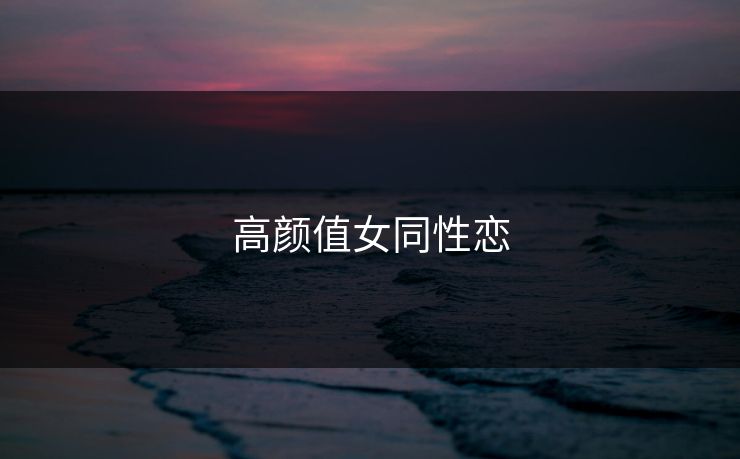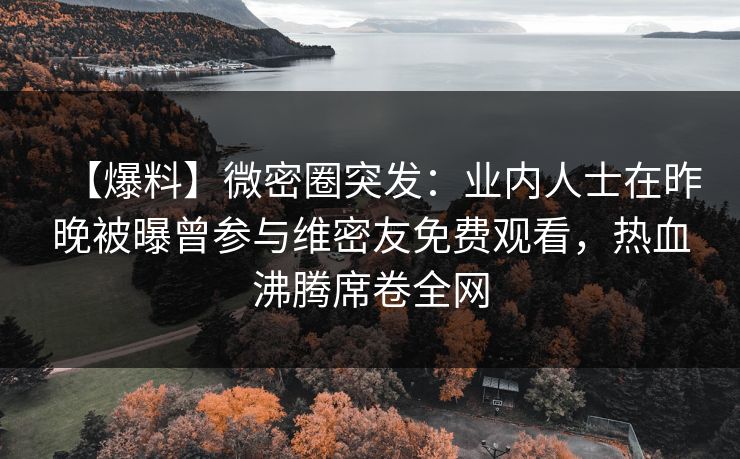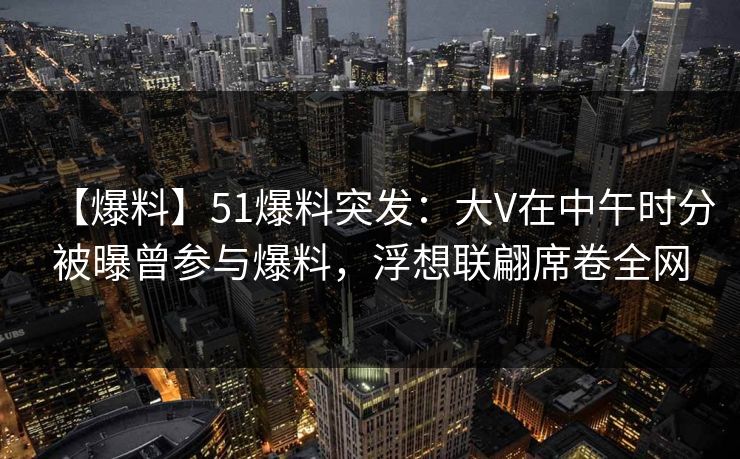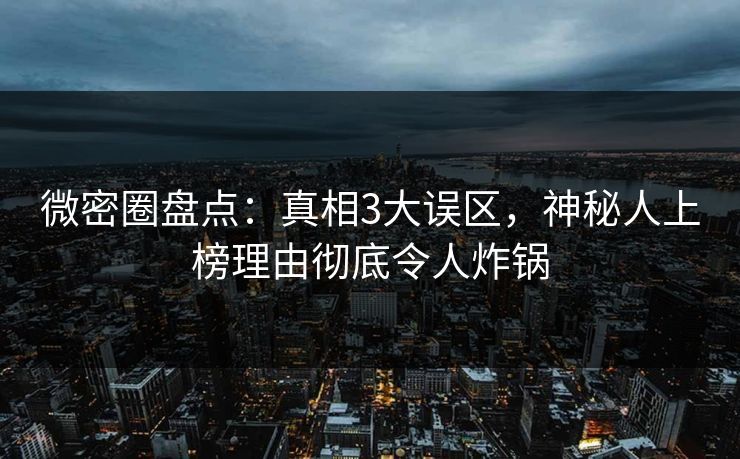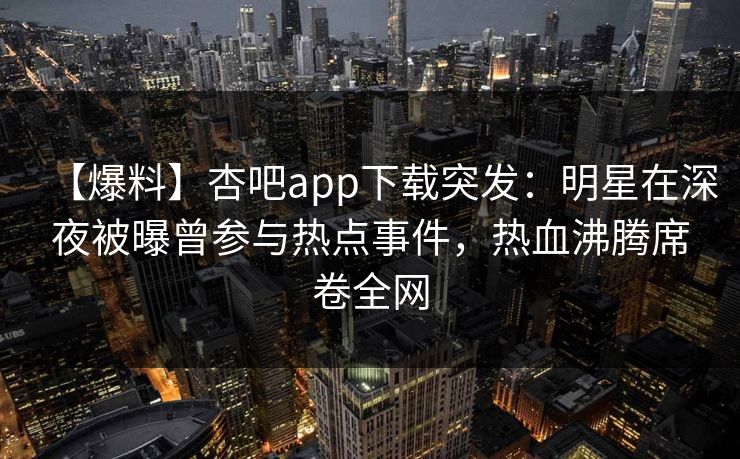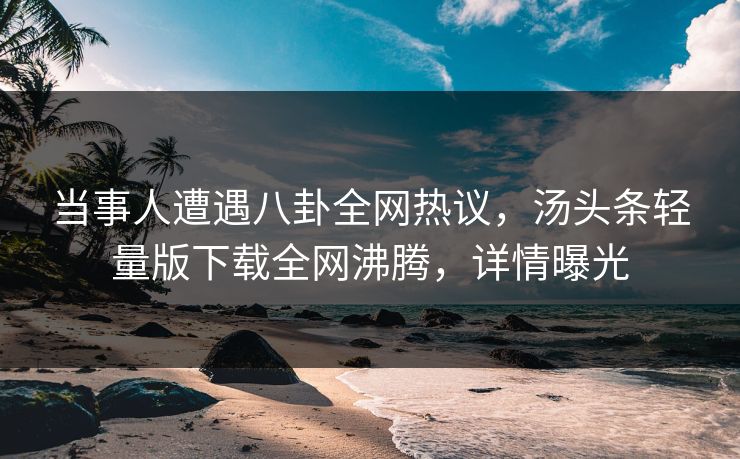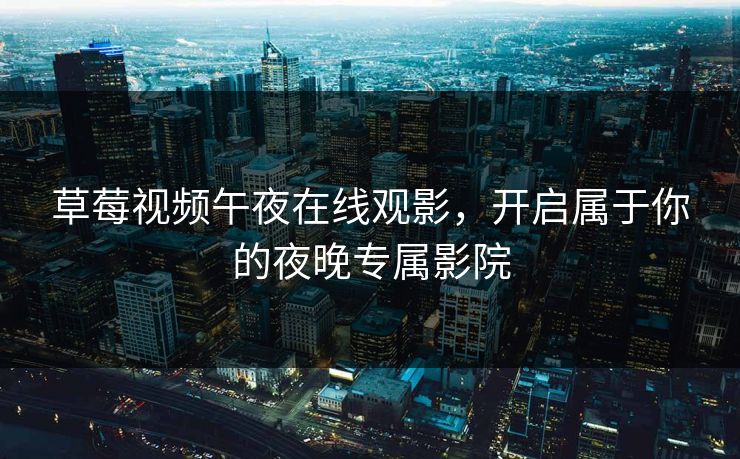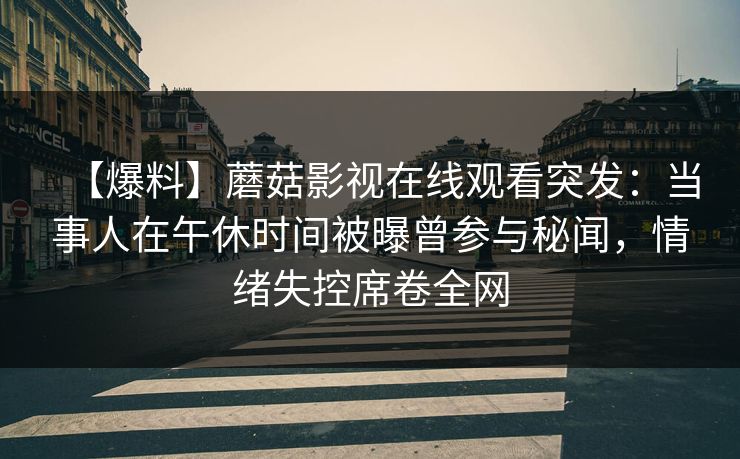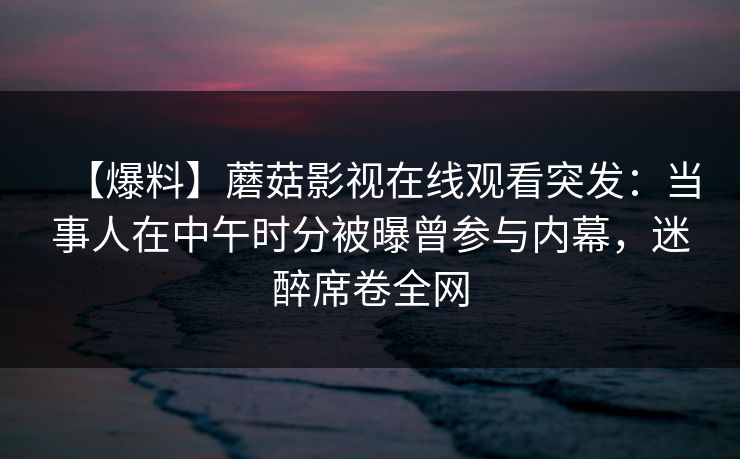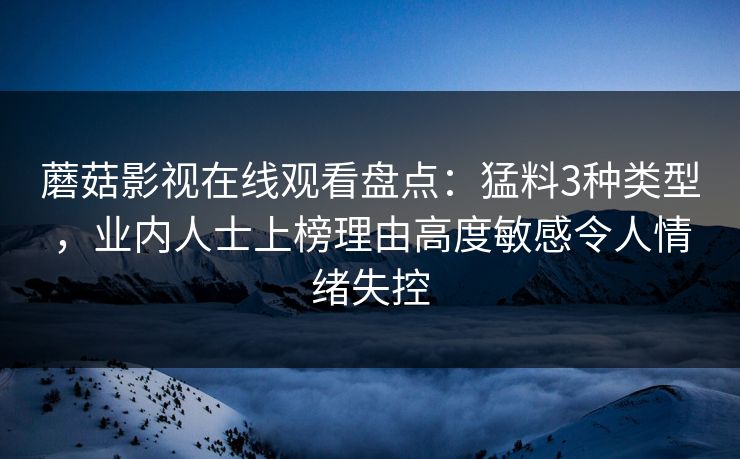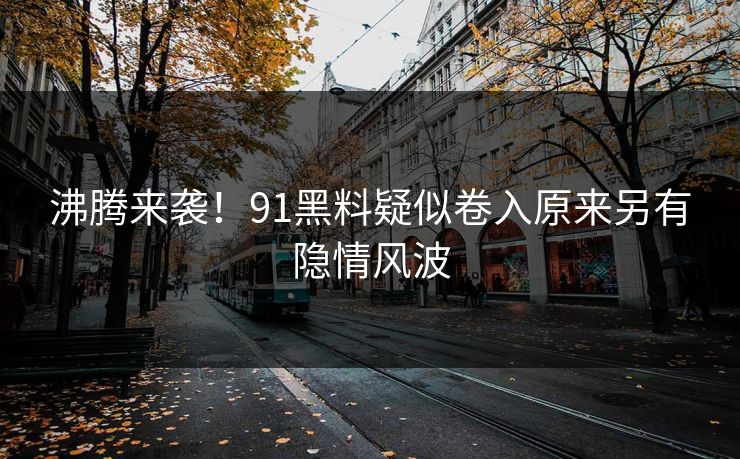老牛耕田陈雪:一曲黄土高坡的生命赞歌
犁铧翻开千层土,老牛踏出万年春
清晨五点半,陕北高原的晨曦还未穿透薄雾,63岁的陈雪已经牵着陪伴他十五年的老黄牛走出窑洞。牛铃叮当作响,在寂静的山谷里传得格外悠远,像是千百年来未曾变过的农耕序曲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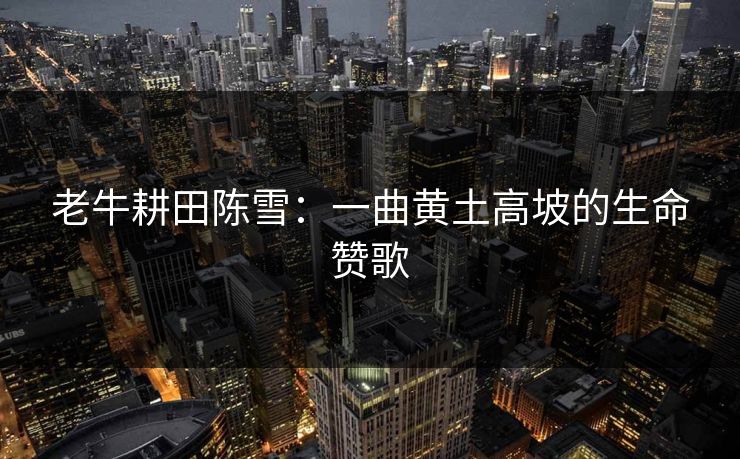
"老伙计,今天咱们要把东头那亩梯田犁完。"陈雪拍拍牛颈,从粗布口袋里抓出一把豆饼喂到牛嘴边。老牛温顺地低头咀嚼,鼻孔喷出白汽,一双沉静的眼睛里倒映着主人布满皱纹的脸。
这样的场景,在陈家沟已经重复了五千多个日夜。村里年轻人都去了城里,只有陈雪和少数几个老人还守着这片黄土地。别人劝他改用拖拉机,他却总是摇头:"机器哪有老牛懂土地?它知道哪里该深犁,哪里该浅耕。"
犁头入土的瞬间,黑褐色的泥土像波浪般翻滚开来,散发出特有的芬芳。陈雪扶犁的双手青筋凸起,每一步都踏得坚实有力。老牛低着头,肌肉绷紧,沉重的犁铧在它身后划出笔直的沟垄。在这片位于北纬35度的黄土高原上,人与牛的配合堪称艺术——陈雪的一个轻声吆喝,老牛就知道该转弯还是直行;老牛的一个响鼻,陈雪就明白该休息片刻。
"这牛比好些人还通人性。"陈雪坐在田埂上歇息时,喜欢摸着牛背絮叨。他记得2008年春天,老牛在生产时难产,他守在牛棚里三天三夜,最后硬是用手帮小牛娩出。从那以后,这牛看他的眼神都不一样了,"像是要把恩情都耕进土地里还给我"。
正午的阳光晒得人发烫,陈雪摘下草帽扇风。远处梯田层叠如浪,新翻的泥土在阳光下闪着油光。他想起父亲生前常说:"庄稼人就像这老牛,低着头干活,抬着头看天。土地从来不会辜负真心待它的人。"如今父亲过世二十年了,这句话却越来越深刻地烙在他心里。
歇够了,陈雪起身拍拍屁股上的土:"走吧老伙计,再耕两趟就收工。"老牛晃晃脑袋,铃铛声重新在山谷间回荡起来。这声音,就像黄土高原的心跳,沉稳,持久,生生不息。
麦浪翻滚岁月深,人与土地共呼吸
傍晚时分,陈雪牵着老牛慢慢往家走。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仿佛要把这一天耕耘的辛劳都刻在大地上。窑洞前的石磨盘上,老伴已经摆好了晚饭——小米粥、蒸土豆和一碟咸菜。
"今天犁了多少?"老伴一边盛粥一边问。"东头那亩都犁完了,明天就能下种。"陈雪蹲在院里的水缸边洗手,老牛自己在圈里嚼着干草,偶尔抬头看看主人。
吃过晚饭,陈雪照例要去牛圈添夜草。月光下的村庄安静得出奇,只有偶尔的犬吠声划破夜空。他摸着老牛温暖的皮毛,想起这些年的变迁:村里通了公路,盖了新学校,很多人家都买了农机具。但对他来说,有些东西永远不能变。
"知道为啥坚持用牛耕田吗?"有一次,城里来的大学生问他。陈雪当时只是笑笑,没有回答。其实他心里明白:拖拉机犁地固然快,但铁犁翻土太狠,会破坏土壤结构;而牛耕深浅适宜,能保持水土,来年庄稼长得更好。更重要的是,这是一种传承——从他爷爷的爷爷那辈起,陈家沟人就是这样耕作的。
去年秋天,陈雪做了个梦,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头老牛,在无边的田野上耕作。醒来后他忽然懂了:人和牛、和土地,早就分不开了。就像黄土高原上的沟壑,看似各自纵横,实则血脉相连。
今年开春时,村里来了个摄影师,非要给陈雪和老牛拍照。照片登上了省里的报纸,标题叫《最后的耕牛》。陈雪让识字的邻居念给他听,文章里写他是"农耕文明的活化石"。他听了只是摇头:"啥化石不化石的,我就是个种地的。"
麦收时节,陈雪站在田埂上,看着金黄的麦浪在风中起伏。老牛在一旁悠闲地反刍,眼神安详。这一刻,他突然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:儿子在城里买了房,孙子考上了大学,而他守住了祖祖辈辈的土地。这片黄土地养活了他家五代人,如今还在继续养育着更多的人。
夕阳西下,陈雪牵着老牛往家走,背影渐渐融入暮色。明天,太阳照常升起,犁铧照常入土,老牛照常前行。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,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改变——就像黄土高原上的风,吹了千百年,依然带着庄稼的味道,带着希望的味道。